《算術題》◎夏瑜滄浪第廿六期 小說坊 2012-08-31今天他想吃乳豬飯,通常他只會吃叉燒飯,又或是油雞飯,再不然就吃燒鴨飯,總之就不會吃乳豬飯。不是因為他不喜歡吃乳豬,他可喜歡吃乳豬,那一年他同鄉的兄弟娶妻,在鄉下家祠前面的空地上擺了二十席,把全村的人都請來了,他還特意回鄉一趟去喝老鄉的喜酒,一般的雞、鴨、魚當然就少不了,主人家還豪氣地每席奉上燒乳豬一隻。那頭乳豬可不得了,他從來就不曾吃過那般好吃的乳豬。乳豬的油香混和著酒氣嬝嬝升起,把家祠的門匾都蒸得閃閃發光。 他知道香港有家富豪飯店有樣享負盛名的菜式叫做「金豬糯米飯」,做法是把糯米飯混和瑤柱花菇炒香,再塞進乳豬的肚子裡,拿到火爐去燒,讓糯米飯盡吸乳豬的香氣,製成後把乳豬從中劏開,香噴噴熱騰騰的糯米飯用來款客,那頭乳豬就像菠蘿炒飯的菠蘿一樣棄掉不吃。他在報章得知有這一種菜式之後,一直搖頭嘆謂此乃暴殄天物。 可是,他很少叫乳豬飯。 他也很少吃叉燒雞飯或雞鵝飯。 單拼飯不論叉燒、雞、鴨,都是廿六元。 雙拼飯不論叉燒、雞、鴨,都是三十二元。 乳豬飯,三十二元。 乳豬雙拼飯,三十八元。 即是說單拼飯比雙拼飯貴六元。 乳豬飯跟雙拼飯同價,都比單拼飯貴六元。 可是,飯還得吃,正如人要活下去一樣。 因潮泛皺的菜牌用膠紙貼在被油污燻得黑亮的牆上,上面用黑色箱頭筆潦草地寫著幾行字,都是草根食糧,近年來物價漲得飛快,菜單的價錢在一年間已不知不覺改了三次,每次都用紙片寫上新的價錢,貼上去把舊的價錢遮住而已。 菜牌上的菜式他根本潦如指掌,可是他還是直勾勾的看著那張菜牌,心中盤算一碟乳豬飯賣三十二元,一碟叉燒飯就賣廿六元,即使說一碟乳豬飯比叉燒飯貴六元。他想吃乳豬飯,省下六元其實還不足以喝一杯熱奶茶,卻足夠他明天午飯時去快餐店買一個特價漢堡飽,吃兩個漢堡飽他就可以挺一個下午,雖然每天到下午四時多他就會覺得餓,可是灌些水他又可以挨到黃昏。這樣想,叉燒飯跟乳豬飯六元的差距就變得很大,大得像是不坐六元的巴士,卻花一百六十元去乘計程車一樣奢侈。 他一邊盯著菜牌上的廿六元和三十二元,眼梢卻偷偷瞄著那個站在櫃檯前的山東大嬸。山東大嬸木無表情,交叉著雙手疊在胸前那塊髒圍裙上,癩蛤蟆似的眼睛盯著那掛在牆角的廿四吋電視,像在看又像不在看,電視螢幕本來該是彩色的,現在所有影象都像是黑、白、灰再掃上一層淡彩,而且電視機好像整天抱怨骨頭痠痛的老頭一樣,不斷發出惹人煩厭的沙啦沙啦聲,根本就聽不見電視播的是什麼聲音。他覺得那個山東大嬸根本不是在看電視,她只是假裝在看電視,然而卻冷眼瞟著他,心裡嘀咕著這個男人到底還要想多久才可以點菜。她也許洞悉了他的心事,知道他心裡那道三十二元減廿六元等於六元的算術題,她打從心底看不起這個男人,她輕蔑他,正如所有人輕蔑窮人一樣,儘管他們從不承認自己輕蔑窮人,因為只有真正有錢的「上等人」才有資格輕蔑窮人。 三十二元減廿六元等於六元是窮人的算術題。 突然,那山東大嬸不再盯著電視,她挑釁似的直接盯著他,一邊走到他身旁,一邊從被她的肥臀擠扁的口袋裡抽出粗製筆記簿,不耐煩地問他:「吃什麼?」他知道他再沒有計算三十二元減廿六元是不是等於六元的餘地,囁嚅著說:「一碟乳豬飯。」語氣連他自己都覺得不肯定。 「叫個套餐吧,有菜、有湯、有餐飲才不過四十二元,一碟乳豬飯都已經三十二元。」山東大嬸的語氣仍是冷冷的,不知是高興還是不高興,就像個調查官邊記錄口供邊跟疑犯說:「你現在招認吧,現在招認刑期減一半。」 他懼怕她的淫威,更懼怕她已洞識他的心事──另一道窮人的算術題:四十二元的套餐比三十二元的乳豬飯貴十元,又比一碟叉燒飯貴十六元。這十六元買到一菜一湯一餐飲,可以買到辛勞一天過後給自已的小小享受,可以買到一個人在茶餐廳獨個兒吃飯也嘗得到在家裡跟家人圍著桌子吃飯有菜有湯的溫暖,那疑幻疑真的溫暖實遠超於十六元的價值。 可是他心中這十六元另有別的價值,省下這十六元他明天就足以吃個午餐,或者加十元晚上就可以吃到油雞飯或燒鴨飯,每天節省十六元,一星期就可以省下一百一十二元,足以支付他來回廣東的車資,也許還有餘錢可以買個「扭蛋玩具」給六歲的兒子,「扭蛋玩具」就是那種在一部機器裡裝了幾十個透明的塑膠圓球,圓球可以掰開分成兩半,裡面裝著不同顏色的機械人或玩具車等諸如此類的玩意,一拉機器的把手,就有一隻塑膠蛋骨碌骨碌地落到出口槽。上次他地盤的工友不知從哪兒弄來一個扭蛋玩具給他,他送給他兒子,小子樂上了半天。 想到兒子的快樂,這四十二元減三十二元或二十六元的算術題就用不著算了:「不要套餐,只要一碟乳豬飯。」其實他已經開始懊悔不該叫乳豬飯,叫叉燒飯就可以多節省六元,六元加四元等於十元就可以買個扭蛋玩具。那山東大嬸卻不就此干休,命令似的:「那就叫杯飲料吧!」這次,他斬釘截鐵地拒絕了。山東大嬸惡狠狠地白了他一眼,隨手丟下那張宛如醫師手寫藥方般難以識辨其所寫的點菜單,嘮叨著扭頭走去料理台前跟另一個瘦得見腮、尖嘴尖耳的女人說話。他暗罵一句:囂張些什麼,下次也不來光顧這爛店。 可是山東大嬸和尖嘴女人仍在討論不休,還不時翻著眼睛向他瞟,跟兩個女人的距離有點遠,電視機仍不斷發出沙卡沙卡的聲浪,他根本聽不到兩個女人在談論什麼,可是他直覺覺得她們就是在談論自己,那個巖山似的山東大嬸一定在嘲他是個窮鬼,窮得捨不得多付十元叫個套餐,窮得捨不得多花一分一毫叫杯飲料。自他坐下來以後那座山東巖就不曾給他好臉色瞧,許是因為他不叫套餐也不叫飲料,是最低消費的那一類客人。 社會上,有錢的人看不起無錢的人,但無錢的人因為自卑,也瞧不起比自己更窮的人。 店裡零散的坐著三個客人,和他一樣,全都是孤身一人,他們身上的衫褲一塊黑一塊灰的風塵樸樸,鞋頭和鞋緣沾滿了泥巴,是燙烙在建築工人身上的服飾,看到「同道中人」讓他感到一陣安慰,很快卻又感到無比沮喪。兩個先他而來的客人,一個已經在低頭猛把菜和飯往嘴裡塞,碟子裡有雞又有叉燒;另外一個津津有味的喝著湯,還把湯骨吸啜出「口雪」「口雪」聲,看來兩個人都叫了套餐。剩下的一人叫的東西還沒來,可是方才他聽見那個人叫的是套餐。換言之,店裡四個客人當中,三個人叫了套餐,沒叫套餐的就唯獨他一個人。也許從來不叫套餐的就只有他一個人,難怪那山東大嬸如此歧視他,社會上窮人很多,可是窮得不多付十元叫份套餐的就好像只有他,如果他就是那四份之一的「一」,他就可能是萬中無一的「唯一」,那他的而且確是個窮鬼的事就成了不爭的事實。 小時候說沒錢是真的沒錢,長大後說沒錢是因為窮。 一想到這裡,他就覺得如坐針氈,電視機在播什麼他根本都看不進去,那兩個大嬸竊竊私語在討論什麼他也開始不太關心,他開始擔心的是另外三名顧客有否發現他就是店裡獨一無二的那個「唯一」。他覺得成為「唯一」實在難堪,如果是世界上唯一能徒手潛水超過四十分鐘或唯一曾登陸火星的地球人自當作別論,現在的情況卻顯然是他是唯一不肯多花十元叫份有菜有湯有餐飲的套餐的人,這個「唯一」使他難堪得像拉了褲子還得在人前站起來一樣。 電視仍在沙拉沙拉吵過不停,但他卻希望這擾人的聲浪能越滾越大,大得可掩飾他內心的尷尬和不安。可貧窮和電視聲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所以他不可能用電視聲浪去淹沒貧窮的恥辱,實在不能。可是他畢竟已多花了六塊錢去將一碟叉燒飯提升到一碟乳豬飯的享受,他不能讓這該死的「唯一」所帶來的恥辱毀了他這頓晚飯的心情,不然那等同坐計程車般奢侈的六元就算是白花了,他是絕對不能讓這種悲劇發生的,絕對不行! 他決定立即好好調整自己的思緒,待會好好享用多花六元買來的乳豬飯,他安慰自己,他並不窮,比他窮的人還多著……電視機仍在發出沙啦沙啦聲……我就是貧窮,也不是罪,認為貧窮是罪才真是一種罪過……電視機繼續沙啦沙啦地響個不停……人家也說「花得起不值得興奮,懂得怎樣去花才是真正學問」,我又不是沒錢吃得好,而是不需要吃得那樣好,乳豬飯已經夠好了……電視機發出的沙啦沙啦聲越來越響,好像靈堂前居士口中唸唸有詞誦經越唸越激昂一樣,終於淹蓋過周遭所有人聲,甚至把他們的身影都隱去,他的心情不期然輕鬆起來,還慢慢開始期待那碟乳豬飯:乳豬飯已經夠好了,一層一咬即裂的芝麻脆皮,蓋著一層厚薄適中散發油香的脂肪,連著嫩肉,每口都是香脆,乳豬飯已經夠好了…… 忽然「啪」的一聲把他從平和的思緒中硬生生地拔了出來,回神一看,摔在他面前的就是那讓他飽受了一整晚折磨的乳豬飯。 看見那碟乳豬飯,他的心情一下子就由期待變成難以置信,由失望復又跌至絕望,就跟那些聚集在電視機旁邊熱切地看著國家的人造衛星第一次在本土發射升空直播的韓國民眾,看著人造衛星成功發射到半空,他們手舞足蹈地歡呼叫囂,熱烈地慶祝國家這一次「勝利」,卻驚見那人造衛星突然在大氣層起火燃燒爆炸,他們盯著電視的眼睛睜得老大不能相信眼前目睹的一切,他們的雙手掩住嘴巴想壓住那一聲驚呼,他們的面上寫著錯愕和絕望,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在烈焰中崩析分離的人造衛星最後化成一群流星似的碎片墜落。 他看見那碟乳豬飯的驚愕和絕望絕不下於那些韓國人。 面前的一碟乳豬飯沒有冒出一絲熱氣,盛得滿滿的白飯上面孤零零的放著五片乳豬件,如像在汪洋上飄零的幾葉浮萍,與那條乾巴巴的青菜正配。乳豬一看便知不是當天燒製的,皮、脂、肉都已經分離,那層本來該是脆如扭麻花一咬即裂的外皮,就像刷過廚房的抹布一樣暗啞皺疊沒有一絲光澤,還冷冰冰的隱隱膩出一陣油味,就似丟在濕淋淋的後巷垃圾籮旁邊的貓飯一樣,沒吃就先倒了胃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多花了六塊錢,換來一肚子恥辱和委曲,竟還買不到一頓像樣的乳豬飯。他覺得他從來就未曾如此委屈過,在毒陽底下付出一天的勞力和汗水,累得四肢八骸都似散開來一般,想好好的慰勞一下肚子,卻只得到沒湯沒菜沒飲料乳豬不是乳豬的一頓晚飯,他過的到底是怎樣的人生?那一刻他真痛恨自己的失敗、潦倒,他覺得貧窮真是罪! 他的眼淚忍不住掉下來落在那碟乳豬飯上,如雨水落在大地滲入泥土消失得無影無踪。他再不理會旁人的目光把白飯一大匙一大匙往嘴裡塞,一大口一大口地和著眼淚狠狠吞下去,好像憑這種狠,他才能宣洩心裡的抑壓、失意、沮喪和挫敗。 他決心要賺很多很多錢,他永遠不要再挨窮。 他發誓不要再算窮人的算術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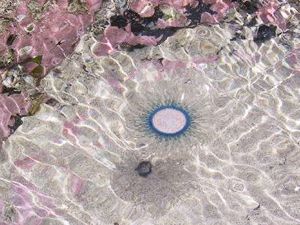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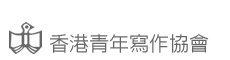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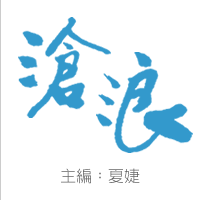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