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快樂》◎小段滄浪第廿六期 小說坊 2012-08-31那天,張耀輝收到一封請柬。 與其說請柬,他更相信是科幻小說、偵探小說裡的神秘邀請。或者他看得衛斯理太多,從小他就是如此把自己代入角色去幻想一個世界一趟旅程的書迷。那是他唯一的嗜好,而且總發生在這時分。特別當他細細撕開信封時,屋裡的夜靜得容許毛孔細語,他更記起那泛黃了的回憶裡的四面牆。吊扇「吱吱」的響,他倒在沙發裡。請柬?咩嚟架?是多少年後的今天呢?他忘了,只記得那時候很小,今天已快二十七歲了,但那幻想的心態還是被自己罰留堂至今。不過,他倒不願去幻想去遇見一個不可思義的神秘主持人了。其實會唔會係外星人?黐線!他壓下自己的好奇,因為他不願意,因為他很認真,因為那請柬裡的署名,是他的母親。 媽媽?咩嚟架? 他看見信末的兩個字時手抖得很厲害。但他的嘴角始終禁不住微微向上揚,心也撲通撲通的跳得異常猛烈。偏偏在喉頭終於拼出一個笑音時,卻滾滾地落下兩行熱淚。赫赫,赫赫……他開始窒息,於是勉強地鎮靜了自己。手還在抖,心仍在撲通撲通的跳,屋子卻一直沒有放聲。他把雙手掩住臉,用掌心稍為擦拭著淚和鼻涕,身體還微微的有點抽搐。信紙滑落腳伴,他彎下腰又縮了回去,然後站起來到廁所洗手洗臉整頓一番,再回去撿起信紙。 他很忐忑。最少,那一晚他到快六時才能不支入睡。翌日醒來,已是下午四時,頭痛欲裂。還好那是星期天,不然新工作又準會被辭退下來,然後又要為糊口苦惱張羅一番。而家咩唧?補償呀?他按著頭暗罵。他記得上一次如此大哭一場還是為了她,他的母親。他其實記不起來了,那時候他才不過五六歲。直至後來相依為命的外婆去世,又或者初進孤兒院時被欺負,都沒有如此哭過。他恨她。他告訴自己,他恨她。 結果星期五,他收到第二封信。 第一封信其實很簡短,只是張請柬模樣的卡片寫著「生日果日見見面。媽媽」。也許他那刻的恨,就因為廿多年來的距離,忽然被壓縮成短短的九個字。一時間,他找不到解壓的軟件,心情便隨之散成亂碼。結果第二封信來時,他就平靜多了。「果日我會去你返工果頭,到時見。」佢點知我返咩工架?佢點知我響邊度返工架?佢點知?佢點知架?佢……他習慣地推理案情,也習慣地猜不出真相,但他總愛猜。 他的生日,是一星期後的星期五。 一星期是甚麼?七天?一百六十八小時?一萬零八十分鐘?還是六十萬零四千八百秒?他大概沒有逐分逐秒去倒數,卻把自己把他的母親把他們僅有的一切化整為零。佢好似好高?好靚?妖!點解會唔記得架?他幻想,他猜。結果,他猜錯了數不完的文件,也猜不中老闆的不滿甚至憤怒,卻猜出了兩封警告信和一封解僱信。他還在幻想,他還在猜。佢究竟係點? 是的,他對解謎從來沒甚麼天分,特別每年家長日同學問起「你爸爸呢?」「你媽媽做咩架?」他都答不上如此艱澀的難題。他試過大哭,試過逃跑,試過發難,然後換來同學們的一場訕笑,畢竟那時候大家還小。沒辦法啊,他怎麼知道呢?他只記得某天早上上幼稚園前媽媽還說:「輝仔生日快樂!媽媽以後每年都買個蛋糕俾你好唔好?快d放學返嚟食蛋糕!」而後,她就隨著三月的霧氣,於日照間銷聲匿跡。「蛋糕呢?」下課回家後他哭著扭外婆:「蛋糕呢?蛋糕呢?」 「媽媽呢?」 那是遲了數年,他才真正意識到的問題,畢竟那時候他還小。就在學校被取笑後的那個晚上,他枕在外婆的膝上問:「媽媽呢?」「我媽媽做咩架?」狹小的四面牆裡,原來搖著蒲扇的外婆止住了手:「媽媽去左第二度做嘢囉,做服務人地果d工。」然後張耀輝多口問了一句「咁我爸爸呢?」 「死左喇!冇喱個人!」 外婆的一喝嚇得他把當天僅餘的淚水都趕了出來。「噯,輝仔乖,唔好喊,婆婆錫返你。噯,婆婆錫晒你……」然後外婆又開始邊搖扇,邊撫著張耀輝的小頭。他瑟縮起來,啜泣,抱緊外婆:「我好掛住爸爸媽媽呀……」「噯,輝仔乖,唔好喊,婆婆錫晒你……」 那天以後,他再沒有如此哭過,即使後來再遇上同學們的追問也沒有。其實也沒多少人會再問他的了,因為他討厭他的同學,他也沒甚麼朋友。 大概有生以來,他只有一個朋友,黃啟昌,他的中學同學。張耀輝記不起他倆如何變得稔熟,只記得他在看《藍血人》時黃啟昌搶了他的書:「識貨喎!好正架喎喱本嘢!」他們差點因此打起架來,卻因為這本書而成為了朋友。「估唔到你都有d料到喎『自閉仔』!」是的,張耀輝是「自閉仔」,他的同學如是說,孤兒院裡的人如是說,因為他徹天徹夜都躲在小說和幻想裡。後來他曾跟黃啟昌說:「可能我都係藍血人。」「黐線!咁我咪超人?」「我始終覺得我同佢地係唔同世界嘅人,我只係得自己一個。」黃啟昌沒再反駁下去:「咪講埋d騎呢嘢喇,食飯啦,好鬼肚餓呀!」張耀輝當然不是藍血人,黃啟昌當然也不是超人,他們都是平凡的人罷了;亦可能是張耀輝說得對,黃啟昌跟其他人都是正常的,只有他自己才是隔在外的另類。 年紀漸長,張耀輝對父母的想像愈漂愈白。他認定自己的父親已死,母親丟下他一個人,不知所蹤。父親打從他生下來就是個沒立墓誌的不存在的魂,是理所當然的無知無覺。但母親呢?縱孩提時也鮮見,但三四歲前,她是確實地有個極模糊的影!她到哪裡去呢?丟下他自己一個,她到哪裡去呢?於是,他告訴自己,他恨她;他也強迫自己,忘記她。他差一點便成功了,黃啟昌的媽媽卻在那時候遇上車禍身故。那晚在公園,他靜靜地看著黃啟昌哭得很厲害,死去活來。張耀輝不懂安慰,黃啟昌明白,他只想找個好朋友陪伴他。哭得沒氣沒力,黃啟昌終於一字一頓地吐了一句:「我好後悔今日落車果陣仲發緊佢脾氣…」然後再次泣不成聲。張耀輝只懂盡兄弟的義務,借出肩膀。他回想起外婆去世的那個傍晚,他好難過,卻沒有如黃啟昌這樣哭、這樣衰傷。點解會咁?他狐疑,然後迷糊間聽見一句似曾相識的說話。 「我好掛住我媽媽呀…」 幾年後,他們大底都忘記了那個晚上。於是當張耀輝在酒吧跟黃啟昌說起請柬的事時,黃啟昌很輕鬆的說:「咪幾好!終於可以見返佢啦!」佢究竟係點嘅呢?「不過,你以前唔係話好憎你呀媽嘅咩?」點解我會唔記得?「喂!有冇聽我講嘢架你?」「吓?」「算喇,早d返去瞓把啦!聽朝又要返工!」「是但啦…都炒左我咯……」「吓?唔係掛?」黃啟昌反替他著急起來。生活怎麼?租金怎樣?還過得去嗎?張耀輝都沒聽在耳裡,心中只管想:「佢究竟係點樣嘅呢?」 那晚他們還談起了從前的生日,張耀輝憶述外婆身前每年都會給他買蛋糕和禮物。「你地唔係好窮嘅咩,佢點會有錢買咁多嘢俾你呀?」「佢錫我嘛,而且有d禮物佢話係親戚送架。」「嘩!點解我冇d咁好嘅親戚架?」黃啟昌失笑。張耀輝又說,後來在孤兒院裡,姑娘也會每年給他買生日蛋糕,直至他離開。「我就唔信喇!係唔係有咁好呀d姑娘?」黃啟昌難以至信。然後話題兜兜轉轉,又回到張耀輝的母親,他又再猜他的母親。「估乜丫,後日咪知囉!」 失魂落魄了一星期,終於又回到星期五。 自收到解僱信後,心不在焉的張耀輝更是遲到早退地幹最後的活。除了今天。上班時間是上午九時,他卻在太陽剛伸展筋骨的時候就起了床。梳洗、穿戴。他準時乘搭平常上班的那班小巴,再步行回公司的大廈。途中,他努力地搜尋。四十歲,尖臉小嘴,長曲髮,整齊的黑色柳條套裝,米白色蕾絲碎花邊恤衫,LV手袋;約五十,鵝蛋臉型,土黃面色,短髮染成橘子紅,束身乾濕長褸。然後的早上,他積極地替公司補送漏了的文件、到銀行入票。四十有五六,紮馬尾,高鼻樑,單鳳眼,紅色粗框眼鏡。然後到附近的茶餐廳午膳。還沒到四十吧?短黑髮,眼小鼻小頭小甚麼都小,卻高高瘦瘦;六、七十,染黑了的髮,根處又露出嶄新的白,Adidas粉紅尼龍運動服。下午再沒跑街的工作可做,張耀輝便坐在位子上乾著急。繼續猜,猜,猜。OL?銀行職員?咩先係服務人地嘅工?茶餐廳伙計?小巴司機?報紙檔小販?嚟我喱頭?快遞?食客?路人甲乙丙丁?老闆看見他早上再如昔般勤快,又為草率解僱他而可惜,於是作重新也是最後一番的讚賞和勉勵。他卻仍是心不在焉,隨便的笑著敷衍。 秒針碎步的踱,還是到了六時正的下班時間。張耀輝草草跟「舊同事」們道別,便離開這個暫寄兩月的辦公室。走出大廈大堂,他先在門旁站定搜索一遍,再沿著大廈附近逛了兩三圈。已經二十七歲的腦袋,還是停不了地推敲著小時的種種幻想。是她嗎?是她嗎?是她嗎?他不停的看,不停的等待,不停的期望四目交投後、會有雙親切的目光迎上自己。是她嗎?是她嗎?是她嗎?今天留意過多少人了?五十個?一百個?還是一千個?他已數不上。是她嗎?是她嗎?是她嗎?「妳響邊?我…我想見妳……我好掛住妳呀!」 街燈下,人由少而多,再由多而少。 步伐愈走愈慢了,張耀輝的心情似乎已跟著夕陽墮進深淵。水泥路彷彿隨他的每一步而愈踏愈重愈黑。他忽然感到萬分乏力。在哪裡?她在哪裡?繃緊的神經終於鬆弛了,不,應該是崩解了。妳響邊?點解妳唔出黎丫?點解?點解?心灰意冷,他開始沒有焦點地走,走到小巴站,屈膝坐在慣坐的尾二排的車輪位子上。 達達達,蓬。 小巴向前愈飛愈快,窗出的風景愈褪愈慢。張耀輝倚著車窗,沒神地看著街景。街裡有上千萬個人,上千萬個女性,上千萬個母親,但哪一個才是她?她在哪裡?天全沒入黑暗中了,只遺下昏黃的燈影在路上濺起片片光暈,綻放淡白的曇花。 「街口燈位有落。」張耀輝被身旁的叫聲驚醒,回過神才發現,原來已快到家門。他忽然嗅到先前沒留意的香水味,濃烈得刺鼻。「好臭!」他心想。車停定,他側頭睨了一眼下車的人。原來是個乾瘦的女人,枯黃膚色,卻穿彩花圖案的情感衣褲,提著盒扶著欄,搖擺著下了車。半秒的背影,其他甚麼都沒看見。他延續了這天突然生成的習慣去審視她,心情卻因整天的尋找不果而格外煩躁:「妖!d咁嘅女人!好彩佢落左車,唔係仲要臭多兩個街口!」 結果,他在下車的街角轉彎的雲吞麵店,吃了他的二十七歲生日晚餐。蓉腩河,一個人靜靜的吃。他想起小時候生日,外婆總會帶他去吃他最愛的蓉腩河,然後回家一起切蛋糕。合指一算,原來已九年沒吃過生日蛋糕了。其實黃啟昌早兩晚也說過要不要跟他慶祝,但當時心裡莫名其妙的暗喜,驅使他婉拒了阿昌的好意。現在回想,倒覺自己太傻。 膳後回家,踏上頹舊的樓梯,竟在閘門外看見一份意外驚喜。 一盒生日蛋糕。 「果然夠兄弟!」張耀輝終於露出二十七歲的第一個微笑,既感動又感激。回到家中切開蛋糕,再拆開信封,讀著生日咭。哈哈!幾靚喎!男人老狗寫咩俾我? 「二十七歲,大個仔喇!」做乜好似呀媽咁架d語氣? 「先前果八年都冇蛋糕食,今年送返九支蠟燭俾你。」咁都記得?好嘢喎! 「記唔記得我以前講過,以後每年生日都會買一個蛋糕俾你?」吓? 「其實我冇忘記過個諾言,不過後來你離開左孤兒院,我冇辦法再叫人送俾你。岩岩響車上面,我好想親手送一次俾你。但見你一路望住窗外邊,又驚你唔認得我,又驚你認左我會尷尬,所以最後都係留返黎俾個驚喜你。廿三年喇,都冇好好咁同你過一次生日,你怪我憎我唔睬我都係應該嘅。對唔住!只可惜,到最後都冇機會。以後冇辦法再買生日蛋糕俾你,但係大個仔喇,廿七歲人,要學識好好地照顧地自己知道嘛?祝你每一日都開開心心!輝仔,生日快樂!」 第三封信了,張耀輝顯得更為平靜。讀著讀著,他忽然記起了從前那一夜黃啟昌哭得聲嘶力歇時的一句話:「我好後悔今日落車果陣仲發緊佢脾氣…」然後,他又想起剛才那個曾在身旁肩並肩的她,顛簸中的半秒背影,無聲無色地下了車。身旁最近的人,有多少個,如此下了車後,我們才發現他們曾經同坐身邊?突然,一滴淚滑落於蛋糕上,白白的,融化得朦朦朧朧。那是張耀輝二十七歲後的第一滴淚,也是最後的一滴;這亦是他有生以來,哭得最厲害的一次。但,他還是很平靜。那晚過後他再也沒有哭過,他告訴自已,每一天都要活得開開心心。 「輝仔,生日快樂!永遠愛你…」 他把生日咭慢慢讀到最後,讀出兩個自己已廿多年沒親口喊過的字。 媽媽。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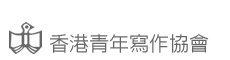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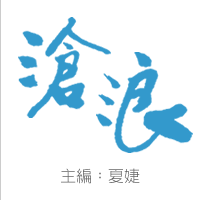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