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他的味道◎鄭裕文滄浪第廿六期 小說坊 2012-08-31我揹著背包,拿著畫家親手繪畫的簡單地圖,照上面的指示,走上一條青石街道。兩旁的街道的路牌均以rua開頭;我記得畫家說過,rua是葡萄牙文街道的意思。 穿梭於一條條充滿異國風情的rua之中,深秋,冷洌的海風吹來,我不自主地抓緊領口;天氣真的涼了很多,畢竟已近十二月了。 不過是想逃避。逃避跟大偉那種糾纏不清的關係,才決定到澳門暫住一陣子。 借住的地方,正是我那位畫家朋友租居處。他要到香港舉行畫展,也順道與他在網上交往已久的同性男友見面。 恰恰就是這麼巧,我得到這個機會,可以去去那個我從未踏足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我與大偉的將來。 畫家早在香港就把門匙給了我,再三教我如何從氹仔碼頭坐巴士到他家;又向我介紹他家附近的概況,包括附近便利店的位置、一家有售賣新鮮刺身的小型超級市場、一家永遠提供熱烘烘豬仔包的麵包店。 還有,畫家特別介紹的那家非常美味的炭燒海鮮店。他說,香港吃海鮮都夠聞名的了,但這家位於氹仔海旁的餐廳的海鮮,足以將香港所有海鮮餐廳比下去。 照著地圖的指示,終於找到了他的家。 那是一棟小小的簡單葡式兩層房子,牆身是奶黃色的,窗門是木製的,沒有窗花。門前有幾盆開著白色小花的植物,整體感覺寧靜而簡單,有種大學時住宿舍的味道。 這時,我豁然明白自小在香港長大的畫家,為何要大費周章的搬來這地方工作,相信這種環境、這種氣氛應可為他帶來不少靈感吧? 站在大門口,將門匙插了進去;不知怎地鑰匙被卡住了,怎樣使勁向左向右扭都毫無反應,拔又拔不出來。我心裡一急,沮喪上了腦,自己居然連做這種小事都不成功!立即想打退堂鼓。 但又記起畫家說過,他住在一樓,而他的樓上另住了一位澳門大學生,於是按了按門鈴,希望這澳門學生還在家。 門鈴按了好久,耐心漸失,在幾乎要放棄的時候,我聽到登登登的下樓聲。 大門打開,露出一雙水靈靈的眼睛,以及一張看來很安靜的臉。 略略地跟他解釋發生了甚麼事;並給他看看畫家給我的手繪地圖,確認一下位置。 他點點頭,替我將鑰匙拔出,並示範扭動的方向;再好心地替我將背包搬到畫家的家門口。不發一言,登登登地又返回二樓了。 畫家的家比我想像中還要簡約。 陽光從窗戶透進來,屋內畫具整齊有序,餐桌上擺放了一束應該是在門前採摘的小白花。是主人特意為我預備的吧? 環視四周,那種一個人流落異地的陌生感、空氣中清冷的味道,突然令我覺得,我離香港好遠、離大偉很遠了。 坐在沙發上,打電話給剛抵達香港的畫家,跟他說了說鑰匙扭不開門的事,也提及樓上那位男生。 畫家說,對方其實也是搬來不久,他與他不熟。但知道他是澳門長大的大學生,主修音樂,喜歡聽古典樂,最愛聽鋼琴;個性比較和靜,有種與人保持距離的友善。 剛掛斷電話,便聽到樓上傳出蕭邦的夜曲。我本身對古典樂並無認識,但因為很喜歡日劇《悠長假期》的關係,戲中的木村拓哉飾演鋼琴家,令我好歹還聽得出這是蕭邦幾首鋼琴奏鳴曲之一。 清涼的音樂在空氣中遊走,我想起剛剛那個澳門男生的樣子,那水靈靈的眼睛,與淡淡的笑容,確實與這音樂給我的感覺相當匹配。 又想起在香港的大偉。他已屆中年,算是一個事業有成的律師吧,卻喜歡在車裡狂播流行曲、手機的背景圖是某個靚模舉起V字手勢泳衣照、喜歡唱卡拉ok,特別愛唱唱方力申與鄧麗欣的合唱曲。愛大口大口的喝啤酒、大口大口的抽煙,愛吃濃味的食物;特別是麻辣火鍋。又喜歡帶我去俗不可耐的時鐘酒店,事後則像海豚一樣呼呼大睡。 我今年二十六歲,跟一個即將四十歲、已婚,並有一子一女的男人這樣在一起,令我自己也覺得自己好老。 我對自己說,早早了結這段關係吧,否則只會泥足深陷,不能自拔。 說實在的,這幾年來,我對男人的口味,已被大衛調教得只有濃厚肥膩,不懂得欣賞清淡優雅了。 我躺在畫家沙發上,不知不覺便睡著了。醒來時,天色已變得漆黑,蕭邦的音樂早已停止了,傳來的是大提琴拉奏的聲音,我不知道樂曲的名字,卻還是一樣令我感覺好寧馨。 肚子開始作響,似有點餓了;這時我才想起──多久,我多久沒感受過這一種令人懷念的空腹感了? 在跟大偉約會的日子,我們總是要吃得肚滿腸肥才安心。一星期總有三、四次,他會駕駛那部開篷的林寶堅尼接我下班,帶我到尖沙咀的酒吧喝兩杯Bloody Mary,他說這是一種醒胃的飲料,然後討論晚餐吃什麼。 大偉身上總是有一陣很強烈的煙草味,由頭髮到嘴巴,什麼時候湊過去都只會令我想起燒焦了的食物味道,就算早上擦牙之後也無補於事。 我想,他之所以如此喜歡吃濃味的食物,大概也是因為抽煙太多令舌頭都麻目了,根本分不出食物原本的味道是吧? 還有,大偉喜歡到名店吃飯。他最愛吃的食物大都顏色很深。比如橋底辣蟹、紅燒元蹄、印度咖哩、韓國泡菜、以及加上滿滿日本芥末的刺身等。每當侍應對這些食物捧到他面前時,他的眼睛都會發亮起來,露出一種動物性的興奮;我印象深刻。 吃完飯後,他往往又喜歡買糖水到時鐘酒店裡調情;買的通常都是又厚又重又稠的甜品。如芝麻糊、花生糊之類。還會要求將一啖又一啖糖水互餵到對方的嘴裡,或將一粒粒糖不甩放到對方身上逐處探索吃完…… 小提琴的樂曲停止了。我聽到有人登登登地下了樓。我也坐了起來。想起畫家曾介紹我去的炭燒海鮮店,決定今晚便要去那裡吃我的晚餐。 炭燒海鮮店於位於黑沙灣的沙灘上,是一橦樸實的平房;可以一邊吃東西一邊聽到海浪聲的一家小店。屋頂有吊燈飾物,在黑色的海灘裡顯得份外光亮。 推門而走進這家小店。 忽有些驚訝。這間店子居然那麼小!中間的櫃台是廚師做菜的地方,客人圍在旁邊坐;大約能容下二十人左右,店內就幾乎沒甚麼空位了。 我找了個位置坐下。扭頭即見,坐在我旁邊的,不正正是住在樓上的澳門大學生嘛?跟他打了一個招呼,他對我靜靜一笑。 因為座位很擠,我們不得不肩貼肩而坐,他身上有種很好聞的薄荷味道。 這家店主要是叫現烤的海鮮,有鹽烤貴妃蚌、鹽烤大蜆、鹽烤大蝦、鹽烤蟶子、鹽烤銀鱈魚、鹽烤黃花魚、鹽烤野菜等等,因為每種東西都看似很好吃的緣故,我看著身邊的澳門大學生叫的作參考,為自己也叫了好幾種食物。 廚師是位大約五十歲左右的大叔,看來有點像葡萄牙與中國的混血兒。他站在櫃台後面,很具功架的用火鉗子將食物反覆翻烤;並且有規律地將食物由大火盆移到到小火盆、或由小火盆挾到大火盆,再一碟一碟地遞到客人面前。 雖然我看不出箇中的玄機,但他烤製的食物仿佛是按照一個特有的章法而調製的。 仔細地咀嚼,發現食物雖然全都是鹽烤,但當中的味道卻豐富得叫我驚訝;有的幼滑、有的鮮甜、有的甘脆、有的微辣、有的具有嚼勁。從來沒想過,只用新鮮的食物、火與鹽三種簡單的元素加起來,便能創造出如此豐富的味道。 這時我又想,對於這樣一家出色食店,只不過能坐十多二十人,不是太過委屈了嗎? 忍不住問身邊的大學生:「你經常來嗎?這店真的太好吃了,為甚麼在旅遊書從來都沒介紹過呢?」 大學生淡淡一笑說:「我也不知道呀,但聽說,廚師先生是故意不做任何宣傳的。聽聞他以前曾是某大酒店的大廚,後來曾在澳門某大賭場開了一家很豪華的海鮮店;但生意太忙了,無法專注調製食物的味道。於是關了那家店,再來這裡開家小小的,賺少許足以過活的錢,過簡單的生活。」 他還介紹我喝店內一種很清香的蘋果茶。 這種蘋果茶跟店內的鹽烤海鮮可說得上是絕配;雖然不含酒精,才兩杯下肚,竟也令我們的心情由初時的拘謹,慢慢放鬆起來了。 我們開始不著邊際的聊天,他告訴我他叫阿森,在澳門長大,現在正在澳門大學唸音樂系碩士一年班。雖然他的爸媽希望他能進賭場工作,但他自己希望將來可以在樂團裡演奏;並且成為一個音樂創作人。 我沒有問他的年紀,但看起來,他應該比我小兩、三歲吧。 我們聊到小店差不多打烊才離開,一起坐巴士回家。 下車之後,就在我們走上青石街道不到一半時,天上竟然下起細細的雨粉來。兩旁的樹葉隨風散落。 我們相視一笑,很有默契般一同奔跑著回家。 我發現他不光是擁有一雙水靈靈的眼睛,而且眼眉也相配得很好看。 進了大門,我們在窄狹的玄關前互相晚安;阿森順手替我撥掉頭上的樹葉。我隱隱地聞到他身上那股薄荷味。目送他登登地上樓。 為了讓自己暖和一點,我倒了一杯熱茶。打開窗子,看著外面清冷的月光。這時,我聽到樓上播起了另一首鋼琴音樂,四周的空氣在樂曲聲凝固。我迷失在旋律之中。 後來,我才知道,那首曲子是德布西的《月光》。 第二天早上,去到畫家介紹的那家麵包店,吃了他推介的熱烘烘豬仔包。 不知是否經過昨夜味覺的洗禮,我咬了一口這簡單卻而美味的豬仔包之後,神奇的事便發生了,我感覺到舌尖味覺似乎已變回靈敏!這是我三年來跟大偉一起,吃過那麼多珍饈百味也不曾體會到的。 開始盡情地做一個全職的旅人。遊覽大三巴、炮台、回歸塔等景點。 也許是那晚的海鮮宴太令人難忘,我對烹飪竟也提起了興趣;偶也跑去澳門圖書館看一些烹飪書。 我發現,燻烤調製海鮮,掌握火候與時間最重要;一般來說,大部份海鮮都要先用大火去烤。但像花枝一類的,則要初時用小火將裡面的內心烤軟,然後轉作大火,這樣才可以令表面香脆,內裡酥軟。貴妃蚌與大蜆可以放在同一個爐裡烤,但就絕不能與扇貝同烤,因為所需時間不同。 烤海鮮,真的是多一分鐘嫌多,少一分鐘嫌少。 閱讀一道道烹調的小貼士。忽然覺得,烹飪──需要的觀察與關懷何其多呀,好的廚師不單要掌握各種食物本身的耐熱程度,就連客人當晚的心情,天氣環境也要掌握。 聯想起自己活過的二十多年,從沒真正地去品味食物。或許也像我一直也未領略過真正戀愛的味道吧。 接下來的日子,我開始獨自在澳門品嚐不同食物的味道。 在澳門,「食」有很多選擇。 初時我主要找葡國菜吃,比如馬介休球、葡國雞、豬仔脾、釀蟹蓋、血鴨等;然而,可能我已學懂分辨食物的原味了,便覺得撒放香料往往太多、多得蓋過了食物的原味。 我還去了幾家西班牙餐廳,吃過幾種西班牙海鮮焗飯;又嚐試各種泰國、義大利、巴西、日本等菜式。雖然有部份也具相當水準,卻沒有一家像那家炭燒海鮮般打動我心的。 或者,我是真的吃過好東西了,以至我越來越懂得分辨好吃與不好吃。 不知不覺地想起以前的日子。有一回,我患了感冒,身體虛弱不得了,大偉問我想吃什麼,我說想吃白粥,最後不知何故還是去吃了四川麻辣火鍋。 可能發燒未退的緣故,當我看著那盤血紅色的火鍋濃湯,吃著那些沾滿老薑、豆鼓、花椒八角等各種味道的肥牛時,我感到頭頂冒煙、四肢酸軟無力,而且勁想吐。最慘的是,在我口乾難耐、眼花混亂之間,竟還硬被他車到時鐘酒店,當我光著那疲弱的身子,瞪著眼看著天花板的鏡子,看到這吃得肚滿腸肥的男子正像野獸一樣的移動身體……突然間,我真的好累好厭倦。 阿森從來沒有主動找過我,也沒有約過我去任何地方。我們偶然會在出入玄關時,點頭打招呼。 有一次,當我一個人在圖書館發獃時,我看到他、也知道他也看見了我,他卻對我視而不見,我有點失望。 心想或者人家不想和自己做朋友也不定呢。他又怎會知道,每個晚上,當他一邊溫習,一邊播起古典樂曲時,其實也為我生活帶來了幾多樂趣? 尤其每當聽到蕭邦的夜曲時,總會想起我初來到的那個晚上,在那小小的店子,吃著一碟碟鹽烤海鮮的滋味。那種在口裡慢慢變化的簡單的滿足感,早已征服了我心中某個部份的感覺了。 有個晚上,我太懷念那家小店的了,於是又坐巴士到了黑沙灣。 微雨斜斜地飄落,客人今晚明顯比上次少了。我隨便找個位置坐了下來,炭烤師傅為我遞上了一碗熱燙燙的葡國薯蓉青菜湯;我身體頓時一暖。隨即點了幾種海鮮,包括鹽燒比目魚、鹽燒帶子、鹽燒生蠔等。 正當我等待師傅像變戲法般將食物烤熟時,有人推門進來。是阿森。 他似乎也有點驚訝會再次在這兒碰見我,向我微笑一下,很自然地坐到我旁邊。 與上次相比,這晚我們明顯熟絡得多了;我問起了他平時愛播的那幾首古典樂的名字,他也對我正在看的偵探小說很感興趣。我們還聊起了喜歡的電影。原來大家都那麼喜歡法國新浪潮的電影……後來,話題落到愛吃的食物上。發現我倆竟然有那麼多共通,例如愛吃梅子排骨但不愛吉烈豬排,愛吃傳統豆腐但不愛吃玉子豆腐等。 自這個飄雨的晚上之後,我在澳門的生活變得精采多了。一有空,阿森便帶著我遊走澳門除了旅遊點之外各個特色地方。我們又會一起到路環那邊的電影院看電影,去圖書館分享看過的小說,走到大三巴附近的路邊攤買最簡單的燒餅,在寒冷的街頭吃清甜的水蟹粥…… 天氣越來越冷,晚上還常常下雨。街頭好冷,總是冷得像是快要結冰;我們於是變成常常獃在他樓上的家裡,一邊喝熱茶一邊聽古典樂。 他有一台破舊的鋼琴,有時他也會即興創作一些簡單的旋律,然後問我的感覺。我發現,他的家跟樓下有頗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室內光線明亮而且整潔非常;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到訪時,發現他在陽台旁有很多小盆栽,問過之後才知道是些歐薄荷,怪不得他身上時時染有這種味道。 就這樣,我們天天在一起。 可是,我們一直沒有發生男女情事,也沒有任何比朋友要親密的行為。或許以後也不會罷。 偶然,我指非常地偶然,我也會想起大偉。 想的是我他的開始,本來就是基於一種濃烈的動物性的慾望,企圖填飽飢餓的肚子,企圖填飽空虛的心靈,而根本從來沒打從心底裡欣賞過對方,亦從來沒有關心過對方。 我想,這段關係是時候做個了斷;如果繼續下去,我知道自己無論在腸胃還是體力都會負荷不了。但想起他知道後的憤怒與歇斯底里,我又有些猶豫。 直到有個晚上,大偉致電給我,說他的老婆公幹去了,問我何時碰面,我才鼓起勇氣叫他以後不要再找我。 我以為我不會難過,但最後我還是淚落。阿森剛巧叩門問我要不要一起聽一張新買的唱碟,當他看到我哭紅了的雙眼,問我是否發生什麼事,我如實的告訴他。他細心地聆聽,說起那次在圖書館,其實他也看見了我,但因為見我似乎有心事,心想我一定遇到了什麼不快事,不好意思上前打擾,所以裝作看不見,免得令我難堪。 為了令我心情恢復過來,雖然已是夜深,阿森還是提議到炭燒海鮮店吃一頓好的。然而,到達黑沙灣的時候,卻發現老闆今天有事早早收了舖。 阿森想起碼頭附近有個天光墟,是海鮮批發市場;我們就去買了一些新鮮的海鮮回家自己弄。 雖然不是用現火烹調,但當看到阿森摺起衣袖,一個人安靜地在狹小的廚房的背影,一時忙著清洗著各種材料,一時忙著燒水,又頻頻看錶免得錯過時間,我還是感動非常。 阿森清蒸的海鮮雖然及不上大叔用火烤的,但別有風味;而且時間也掌握得剛剛好,我想,這是跟他本身是學習古典樂有關的吧。 晚深,我們不算聊得特別多;但拉赫曼尼諾夫鋼琴奏鳴曲在室內漫流,吃著那些自家製的清蒸海鮮,喝著那些微溫的清酒,我還是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默契與幸福感。 我不知道這種幸運的感覺可以持續多久,但至少我知道這不是一種動物性的衝動,而是像阿森烹調的食物一樣,有著一份溫柔、細心、平實的味道。 天快要亮了,酒精也開始在我體內發熱遊竄;帶著點點醉意,正打算返回樓下,阿森突然伸手出來拉住我的手腕,將身體靠向我,輕輕的對我說:「留下來,好嗎?」 接下來發生的事,細節我不是記得很清楚了。我只記得,跟阿森做愛,與跟大偉可說是兩碼子的事。阿森的身上有著一種淡淡的薄荷味,他很懂得掌握性愛的節奏,就像一個出色的廚師一樣,熟悉每個食材的敏感特質,順著我的情緒起伏去移動身體,時而溫柔,時而激動,這跟大偉那種帶著獸性,一心只想征服的火辣式做愛的感覺是很不同的。 在澳門停留了四個月。暮春,畫家歸來,我也返回了香港。 離開時,阿森送了一盆他栽種的歐薄荷給我。 把歐薄荷帶回香港,放在窗台上。每天它會迎來射進我家的第一抹陽光。 當然,我和大偉已是陌路人。我也不曾重訪澳門。 每當微風拂過窗台上歐薄荷,我會記起澳門的青石街道;還那家炭燒海鮮店、那些古典樂,與一個身上有著薄荷味道的男人。 還有他在某年某月曾為我帶來那種恬靜的溫柔。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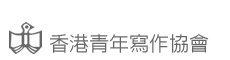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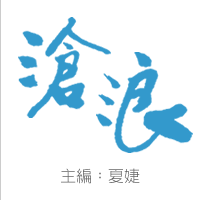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