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失的貓◎劉耀文滄浪第廿五期 小說坊 2009-01-13我經常會做一些奇異的夢。 例如我在黑夜的街道上走壁飛簷、又或者在晨霧迷惘的草地上走著之類。四周有很多貓看著我。不過我從來沒有認真對待過這些夢,直到我又重新認識一個老朋友。 我想起她的,更多是關於她的家人。我很少認認真真地覺得有甚麼人真的很友善,大抵他們是其中之一。我記得她的媽媽是個五十幾歲的女人,一手好廚藝,我記得她的烤薄餅,竟然一度成為一陣子我到他們家去的一個借口。她會弄的還有熱香餅,都是很西式的料理。反而他們自己國家的料理,我卻沒有機會嚐到。留意到了嗎?我說料理。因為我以為自己會在日裔的她們的手中,嚐到日本的料理。雖然我對吃從來沒有甚麼嚴重的心癮。 她的祖母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亦是日本所謂的「開拓團」成員,當時他們被政府「號召」到中國東北去,每個都懷著「東北到處是大豆和糧食」的夢想,成為日本軍政府那顯然妄想的殖民大計裡的棋子。當時的東北叫作「滿洲」,我們的清朝未代皇帝就在此當傀儡皇帝的時候,她的祖母就是那開拓團的成員之一,在日本戰敗之後在東北的日本人大多無力回國,他們塞在長春市的大街小巷、塞在火車站與鐵道之上打算回國。這些日本人當然沒有任何工作、沒有生計,也沒有保障。而日本政府當然自身難保,更不會管身在中國大地的日本人。 顯然而見,那時,孩子顯然成了他們的拖累。有些日本人弄死了自己的孩子、懂漢語的就哀求中國人收留他們的孩子。現在聽來好像是很難想像的東西,你會說甚麼虎毒不食子,可是人類從來不比動物高貴多少,那兵荒馬亂的春秋,於是人性就暴露出最原始而真實的一面。各人有各人的選擇,有人選擇了結自己的孩子免他們受苦,沒有對和錯,世間似乎只有強權而沒有對錯。 後來她們知道,當時大約有五千人個孤兒留在東北。多集中於滿洲當時的首都長春市。後來不少中國家庭收養了他們。有好些還是嘗過日軍侵略之苦的人,不過他們就是收養了這些來自日本的孩子。他們最大的不過十來歲,最小的可能是手抱的嬰兒。 她的祖母是這五千人之中的其中一個,她們被一戶算是富裕的米商人家收養了。因為當時那家人的夫婦不育的關係,她的祖母在這戶無兒無女的家中得到了寵愛,二十幾歲的時候她結婚了,生了她的媽,然後他們南下,不再住在中國了,於是她們來到了我們的城市──曾經的小小漁村,現已成為某個不中不西的西式小城。 在這塊似乎總是太平盛世的地上聽著她們的故事,總覺奇異之感。不是嗎?這裡是太平的,我們既沒有受過戰亂之苦、亦未嘗文革之時的批鬥文化之禍,我們的上一代當然亦未嘗過下鄉接受貧下中養的「再教育」。甚至,一直以來在英國的管治之下,這個小城似乎比她的祖國發展得更好,於是這裡出現了中產、出現了富裕。甚至我們不需要忍受政治的愚民封鎖政策,更可以在網路上暢通無阻地行駛。 我們總是窩在一起看電影。我們不喜歡到人多的電影院裡。其實想想也很沒趣,偏偏我們一般人看電影都有種不成文的習慣:總是得與誰人結伴才能成行。大抵我們之中也沒有太多人「獨自上電影院」吧。我們喜歡看電影,她喜歡拉我看恐怖片。她對恐怖片有種近似宗教般的狂熱,可是她從來不會因為看電影而尖叫之類,她沒有這種反應,我一直覺得她的耐嚇程度甚至比我自己要高。她喜歡看恐怖片,又會孜孜不怠地談著電影中的某些橋段。從近期回到畫質奇差的舊片,無一不看。 我喜歡的電影種類比較雜一點,特別偏愛西片。千軍萬馬的大製作也非常愛看。於是每個星期六我會見她,一如她會見我一樣。將我們各自的朋友隔絕在外,只有我們。彷彿要把那張放在客廳的沙發也磨爛一樣,通常好很安靜地看,然後談個熱烈。大概是這樣。 我希望自己的記憶還管用。 她的家一直有養貓。養了三隻貓。我總是到那裡去玩她的貓。我實在喜歡那些小巧的貓科動物,難得的是牠們非常乖巧,讓我抱抱摸摸,懵懵懂懂的神情最討人喜歡。可我很沒心肝地從來分不清牠們的名字、模樣……不打緊,那成為了我們最後之前的時光的美好,成為了聚首的借口。當有天電影也看得太多的時候。 因為日本有小泉純一郎的關係,曾經在記憶的潮水中染上中國的反日浪潮的一點悸動。她曾經這樣問過:「你覺得示威的人怎麼樣?」 當時我在調校那好像失靈的光碟機。停了下來,因為我不曾想過她會注意,又或是我會認真地答她。 「沒有甚麼,但想深一層其實是很弔詭的,中國政府是不容許人民聚黨結社的,可是那些中國人卻能在日資工司鬧事,又或是在街上示威。卻沒有公安阻止。」我對她說。 她坐在她祖母死後留下來安樂椅上,很安靜,似化成石像一尊,可那是思考的僵硬。我總是迷戀那沉思的安靜,像在臉龐用安靜紛飾妝容一樣。我在她的臉上找到其他女孩甚至男孩也沒有的靈巧。這是很重要的,大抵在俗世層面上她有時安靜得有點異常,可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也是怪哉之人? 當時陽光正仁慈地灑落,星期三的下午兩點,世界暫時陷入安靜之中。就像上班上學族陷入午飯之後那飯氣攻心的沉睡之中。春未的陽光,剛好劃過那些貓的毛織似的脊背。 「你總對這些事情不很關心。」她說。 「就像妳一樣,難道妳又關心?」我反問。 她笑。「對,我不關心。反正關心也不能改變甚麼。」 唉,我愛死了她說這話的模樣。反正關心也不能改變甚麼。 「可是愛國不是很重要嗎?那些公民教育。」她又問。 「噢,那只是狗屁。」我說。 「通常戰爭也是因為兩國之間有等量的老古董愛國者。」唉,說到這些教育問題我總是口水多多,話總是不停。 她一直微笑,不說甚麼。彷彿是看到她即將「進入正題」的臉,然後,她果真開口說話:「我做了個奇怪的夢。」 這時我們聽到樓上傳來似乎是一對男女正在做愛而發出的喘氣聲。還有附近時不時傳來的狗吠聲。大概是因為舊樓,隔音不好。我說。 她搖了搖頭。「因為現在很靜,只有我們。」 大抵,我應該聽懂這句話的。不過我沒有。 「我做了個夢。我夢到你從小咖啡的背脊跑出來。」她說。 聽了,我頓了幾秒。小咖啡是她一隻咖啡色的小貓,剛滿一歲,她最寵牠。我比較喜歡那隻老貓,聽說已經十歲了,可是滿身白色的毛和那智者般的神情,總是優雅,我喜歡。 「我從牠的背脊跑出來?」我聽到自己的話中帶點笑意。 「對呀。」她說。 她穿得那麼單薄,如我在長長的牛仔褲之外的那雙赤腳一樣裸袒而涼快。白皙修長的頸子就是性感,可我知道那只是我的一套審美觀在作祟。她實非年輕男生所喜愛的那種甜得彷要漏出蜜糖的女孩,她亦非很男孩性格,更難走入男孩的圈子。她甚麼都不是。笑容其實很少,說話直接得有時會把人嚇倒。 「我聽見班上的男孩在談A,她很受歡迎。」我以前這樣對她說。 當時她有點冷地笑了笑。「噢,她每天都要扯著喉嚨嬌滴滴地說話,其實我真替她辛苦。」 可憐她總是遊離之眾。 「你不會知道,女生是種麻煩得要命的動物,她們天生喜歡說三道四,沒完沒了、沒完沒了。」 「所謂的天生八婆嗎。」我問。 她大笑。 「我不知道為甚麼會做這種夢。」 「夢都是有含義的。」我說。 那時是夏未。白天氣溫總是高得難耐,但其實我頗喜歡夏夜,空氣沁涼,望天,石屎森林的圍困中似乎還有一絲暑熱後的清涼。來電,她告訴我:「我談戀愛了。」我覺得那是奇聞。我有興趣的是:她會嗎? 「噢,我很有興趣那是個怎樣厲害和特別的人物。」另一邊傳來似笑非笑、彷嘆非嘆的聲音。 「你錯了,那是個悶蛋,甚麼也不懂。只懂得K歌、遊戲和讀書的悶蛋。」她淡淡地說。 「噢,那一定是個很正常的十幾歲男生。完全不像我的。」我說。 「是呀。你不會從他口中聽到一點有趣的東西。對音樂的認識還留在名星和K歌的階段之類之類。」 「可是,妳又選他?」我問。 「嗯,我也不知道為甚麼。也許我只是想刺激你一下。」 「真的?」 「也許。」她的聲音像我的一樣,那樣不急,緩急有序。 「可是我知道自己永遠也無法再像他們一樣。因為我的一切都是妳教我的。是妳使我開悟的。」我說。 「也許。也許我有一點後悔。」她又說。 可是或許我現在還會覺得奇怪,我既是見過那個男孩(果真如她所形容的一樣,唉,層次問題,非他之過),可是她依然讓我抱讓我吻。安靜地任我而為。 為甚麼?我問。有天,依然是甚麼都不是的空白下午。 「火靠近蠟燭就自然會發光,我也不知道為甚麼。」她說。 「你是蠟燭,還是火?」我問。 「有分別嗎?」她少有地笑得很甜。 她的媽跟我的媽彼此也認識,關係似乎不錯的樣子。她們經常會神秘地談著話。我所說的神秘並不是小聲說大聲笑的那種,那只是一種姿態,她們以「女人的方式」保持著微笑,談話。你會發覺自己從來不會知道她們的心思。不過她還是善意的。她的媽有時會跟我說說話,例如我在幫她把烙好的東西拿出來,在廚房裡的小小空間∕空閒。 這個五十來歲的女人保養得很好,大抵是身形向來瘦削的關係。臉上有不少皺紋,可是那些皺紋彷彿成就了優雅。她把她小時候的一件事告訴了我。知道了以後我跟她的相處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只是我也不能欺騙自己說這完全沒有改變了我心中的甚麼。 她的媽媽說,當時她七歲,她們還在中國生活,而七歲的她曾經被一個十幾歲鄰居侵犯過。她說當時有想過報案,可是七歲的她事後說甚麼也不記得。證人也沒有。最後就此不了了之。不過幸好沒留下甚麼東西。不過心裡的就不知道。其實這件事大抵也成就了她們離開又離開,逃離又逃離。 「那孩子的心大概已被甚麼損毀了。所以她有時會很怪,請你多照顧她。」 我口裡稱好,可是心裡卻非如此認同。大抵我也是受傷的一個,凡人、我們若是夠細膩敏感,對世界有一丁點感悟,也總會被這個世界刺傷。因為我們想去觸摸。我們大多數人都多多少少有心病,可是分別在於我們會不去看那疤痕,或是在自己一個的時候才好好凝視、細看、觸摸、痛楚。 「妳們會回日本嗎?」我問。 其實這句話我雕琢了很久,而這是我認為最好的問法。因為我想過「妳們在日本有親人嗎?」之類的,可是那似乎太敏感了。也似乎不太切合我這麼一個後輩的身份。 她笑了笑,用最優雅的方式引開了話題。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她把「已經分手」的消息告訴我。 那時還是早晨時份,我還未起床,可是讓我全醒來的是第二個消息:「貓都跑了。」 究竟她是怎樣把三隻貓全都掉失了,我不清楚。可是在走那條老街的時候我才記起,我昨晚也做了夢,夢中我自她的家裡離開,不知為何我走得很急,然後一直跑過那些老房,沒入一片荒草亂生之中。然後夢就結束了。這是歷來影像最清晰的其中一個夢。 我們一起在山坡旁邊的小路找著三隻貓的蹤影。她的眼有點腫,像睡眠不足多於哭過。她不會哭的,至少在我哭之前。 最後我們找到兩隻老貓,牠們佇立在草地上好像等著我們似的。可就是不見她最寵的小咖啡。一直走著,我把牠們帶進早就帶來了的大袋子裡背著,一直看著她的背走著,那一道垂落撩動的髮際總是分散我的注意力。在黃昏之前我們終於找到了那隻小貓,牠好像被附近的狗咬過,又好像是曾經掉到甚麼地方似的。遠遠看來我以為是塊形狀差了點的石頭,原來是捲著身子的咖啡色小貓。 最後還是把牠帶了回去,七點鐘我離開了,她們照顧好那隻小貓。兩隻老貓很聰明地找到找尋牠們的我們,而小咖啡也許太年輕了,牠不懂,也沒有老貓們的老成和智慧。 凌晨的時候,她說:「抱歉,你睡了嗎?」 「我是早餐派。」我說。雖然我已知她電話訊號的來意。 「牠救不活了。媽把牠帶給街上的獸醫看要怎麼辦。」她的聲音乾乾冷冷,還是如此冷。我一直在想,為甚麼她的貓會全跑了。我無法不把她跟那個「乏味無比」的男孩分手的事情與之聯成一線地思考。可是中間我們又需要深究嗎?結果擺在我們面前,無法改變。 那一晚之後一切如常。會有甚麼改變嗎?最初我這樣以為,可是她沒變,又是她。 又回復跟我短短的距離,在下午小聚一下,我也沒變,由此到終我也是旁觀者。雖然我旁觀,而對一切無力。有時不看電影,並肩經過老街,來到當日尋貓的那道通上連綿山巒的小山道,黃昏的暗淡,日本的傳說中,相傳黃昏即是「逢魔之刻」,是陰陽交錯、鬼神開始出沒的時間。我會想起這小小傳說,是因為我總是會看見一隻咖啡色的小貓經過我們身邊,擦過青草、踢走小石,走得奔奔跳跳。 那絕非幻像,小貓之現實,就像她的手的觸感那樣真實。牠有時還會抬頭看看我們。可是每一次當我提及小貓的出現。她也一臉疑惑:她完全看不到。我形容牠的特徵,然後,此景此情,她想到自己曾經的寵兒和愛貓。於是她有時會自己「散步」,可是她從來沒有見過任何貓隻在附近出現。 她最想見,但始終不曾見過。只有我或是她的母親(對,她的媽媽有時也會看到)能看到聽到。在那之後,我那些斷斷續續的夢卻轉了主題。我不再看見其他貓,也不再夢見城市,在夢中我反而總是在山野跑跳和漫遊。在夢中像靈魂得著了自由。星月流水反而成為了夢中迷糊的符號。 也許有天夢醒,我們發覺夢與非夢亦是真實。也許這樣的世界,更添一種複雜的感覺。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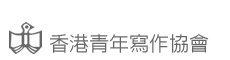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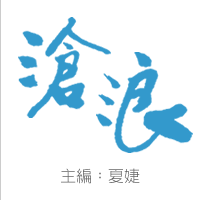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