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的層累—論稼軒詞〈惜分飛春思〉◎蒹葭滄浪第廿五期 詩世界 2009-01-13翡翠樓前芳草路,寶馬墜鞭暫駐。最是周郎顧,尊前幾度歌聲誤。 稼軒這首〈惜分飛〉,本不算甚麼「黃絹幼婦外孫齏臼」,但喜歡玩典故、化用前人語句的現代人,倒可以學一學這首詞的作法。恭三先生《稼軒詞編年箋註》〈增訂三版題記〉提到「其在詞藻方面,則融經鑄史,驅遣自如,原為辛詞勝場之一」。迦陵先生在〈論辛棄疾詞〉中認為辛詞多用典是因為「本身原具有強烈的感發之資質,其寫景與用典並不僅是由於有心以之為託喻,而且也是由於他對於眼前之景物及心中之古典本來就有一種豐富的聯想及強烈的感發……」。換言之,辛詞之用典並非為了用典而用典,而是另有隱意。照這樣看來,在讀辛詞的時候,政治學家Leo Strauss的「字裡行間細讀法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可謂有用武之地了。 所謂辛詞另有「隱意」之說,我原則上讚同。尤其像〈摸魚兒更難消幾番風雨〉這樣的作品,確是三閭遺風。「幾番風雨」、「春又歸去」、「長怕花開早」、「落紅無數」、芳草無歸路」、「盡日惹飛絮」、「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脈脈此情誰訴」、「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曰其不怨,孰能有信?這種較容易看出來的名作,解人必多,如羅大經,如謝枋得。其實和辛詞韻的趙善括也知道內裡的意思,要不然和詞下片就不會寫「望故國江山,東風吹淚,渺渺在何處」了。好了,扯遠了,就此打住。我們且回看〈惜分飛〉這一闋詞。 首句「翡翠樓前芳草路, 寶馬墜鞭暫駐」。晚唐韋浣花〈木蘭花〉詩有「獨上小樓春欲暮,愁望玉關芳草路」之語。原詩在《浣花集》中並不出名,也非上佳之作。同樣採用「樓」和「路」的意像,同叔「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氣韻實遠勝矣。要之氣短本《花間》通病耳。稼軒事功、文章兩者得兼,長調小詞無所不能,揣其心意,斷不肯受制於花間小詞。首句已有心抗禦之。至於「墜鞭」,本是小說傳奇中的風流雅事,唐人傳奇〈李娃傳〉(明人徐霖的《繡襦記》即本於此,為崑曲明劇)「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 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 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従者,敕取之,累眄於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據此則本詞應有男女相遇互慕的意味在裡頭,而且女方應該還是歌女出身一類,聯想到題目為〈惜分飛〉(此牌為毛滂所創,專為詠唱別情之用),似乎亦含有一點男女相遇而後別的情境。實情如何?且再看下去。 「最是周郎顧,尊前幾度歌聲誤」。這是很通俗的典故了。典出《三國志。吳書。周瑜傳》:「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尊前清歌曼舞,似乎是宴飲場合。起句似乎暗示了緣起(寫作動機)和主題,而這一句則是交待地點。要注意的是古人寫作與今人不同,尤其是古典詩詞,非常注重意象的跳跃感。至於西方文論Aristotle針對時間、地點、表演主題一致性的三一律(Unities),在批評中國詩詞時並不是適當分析工具。正如這首詞所見,從主題到地點,其中都存在著大量的不確定因素,單看上片,讀者只能就文本主題大概摸到一個框架,而裡面東西其實都是可變化(flexible)的柔性質料。主題是否真的有男女相慕之事,〈惜分飛〉的別情是否男女之別--我們盡可以想像為稼軒與一位歌女相遇而暫別的風流韻事—還是未定之數,而且宴飲地點也沒有具體交代,受眾這種模模糊糊的未知感正是作者得意處。不同於現實主義的作品,中國古典文學的不少作者都不講求受眾領悟,他們所求的是「解人」,即真正的知音,最具體的表現就是作者互相唱和之習慣。在一般人眾中普及並非他們的主流常態(當然特例也有不少,最著者是老嫗能解的白樂天詩)。這是一種文學欣賞/批評方面赤裸裸的精英心態,但必須承認,這種心態在創作上會帶來更具「巧思」(Ingenuity)的文本,尤以詩為最。由於不必要執著時、地、人、主題、意象幾者的邏輯統一,跳跃的可能性就大大加強了。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西方現代派或先鋒主義影響下的一些技巧乃至實驗,一早就在中國詩詞裡被廣泛接受和承認了。例如文本獨立的生命(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詮釋空間的強調(言不盡意/意在言外),詞組結構的顛覆(工部《秋興八首》)……正因為古典文學的文本在當時人/唱和者/後世受眾猜測揣度中不斷成長,所以成為了真正的詮釋迷宮(labyrinth)。而被巧思串連起來的文本們通過典故彼此呼應、對話,今古之情無間,所以稼軒可以隨時請出韋浣花、白行簡(〈李娃傳〉作者)—下面他還會請屯田、長吉、青蓮,還有才盡的江郎—來幫手。在他們已有的文本基礎上,織出更複雜的圖案,我稱其為古典文學中之「典故的層累」。我們試以下片稍為分析。 「望斷碧雲空日暮,流水桃源何處」。第一個七字句至少化用了兩個典,一個是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中「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之名句。辛詞用了「碧雲」、「日暮」的意象,而且是「望斷」,那麼他隱喻了的東西就很明顯了,就是未來的佳人。至此則上片之猜測更形真確。別離的時候,不見佳人,君子悵然。柳屯田〈洞仙歌〉「傷心最苦,竚立對碧雲將暮」正好也是男女別離之意,至此對稼軒詞的主題又有了進一步瞭解。但要注意,稼軒不會寫像「望斷碧雲空日暮,回首佳人何處」這樣的句子,如果要這麼累贅才能把典故提示出來,只能說是不善用典。要之,費盡苦心讓每一個讀者明白其詞意,像稼軒這樣的天才絕不屑為。把數層典故疊在一起,而且把根本沒有寫出來的典故出處下半句也織進讀者的聯想之網,這才是稼軒用典精妙絕人處。理解了這一點,才能更好把握恭三先生稱頌稼軒用典「驅遣自如」四字真義。 至於「流水桃源何處」,乍看下大都知道是用了五柳〈桃花源記〉的典。但是,這裡有一個微妙之處,桃源固然因五柳而見稱,但桃花源〈詩〉和〈記〉皆無「流水」一詞。稍加深入探究,即可知「流水桃源」是由青蓮〈古風〉化用而來:「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這才是此典完整的出處。青蓮詩所謂「千春隔流水」,主題在於入桃花源後與世隔離的感發。而稼軒詞講「別」意,正與之相呼應。如此一來,兩相通透,充份發揮了「典故的層累」希望達到深化文本意蘊的目標。 最末一句「聞道春歸去,更無人管飄紅雨」,上句用山谷「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典,取其後句寂寞意;下句用長吉「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的典,取其前句青春早逝之意。這裡也是一樣,稼軒化用在自己詞裡頭的不是主題,象外之意才是。這裡的寂寞與青春早逝,與男女之別似無直接關係。事實上,我們一直都忽略了一個問題,男「女」相遇的「女」,非要是人麼?稼軒作品和三閭大夫的很像,而三閭最著名手法就是蘭若、君子、美人以喻君臣的隱語。這首小詞,固不敢說一定有〈離騷〉「眾女嫉余之蛾眉兮」的大義在裡頭,然而最後一句突兀如此,而前面解釋亦多為揣測之辭,恐亦不為無因。這是否另一首如〈摸魚兒〉般的刺怨之詩?恐怕是大有想像餘地的一件事。我想說的是,之所以造成這種豐富的聯想空間,說到底,正是稼軒運用「典故的層累」爐火純青的表現。稼軒有一首〈浣溪沙〉尾句我很喜歡: 「幾時高處見層軒?」 在欣賞辛詞一層層的典故迷宮中,正是這種感覺。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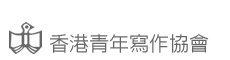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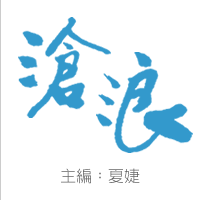 |